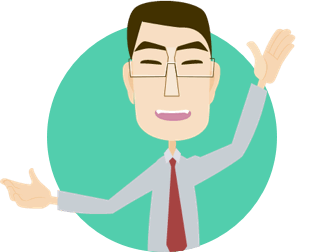南村的想想
发布于2017-11-22 宝宝1岁时
《一岁记》 一恍,又是一个冬天了。 今天是农历十月初五,小雪时节并未落雪,却是想想生辰的正日子。不敢想,去年今日努力诞下的小人儿,今已一岁了。古语道“儿奔生,娘奔死”,把生命的轮回与孩子的长成、母亲的老去联系到一块,多了一丝只有为人母者才能体会的酸楚。 外子与母亲闲聊,说起小女生日,母亲在电话那头说:好好犒劳一下燕子吧,想想的生日也是她的受难日…… 那我的生日何尝不是她的受难日? 二十七年前的初秋,母亲在外婆家吃了最后一顿公鸡饭,有了临产征兆,被外婆催着赶回她婆家,说吃了鸡公有力气。乡下女人生孩子,没有助产医生,也没有任何医疗措施,痛的死去活来的时候就把接生婆喊来。我们那里是水乡,车马很少,村里人要过岸都是撑竹排渡河。接生是两条人命的大事,耽误不得,急得团团转的父亲点了一把油火就下河去了。山里秋夜露冷,白月如昼,草木枯黄,但河岸两边的芦苇和香蒲仍然绿着,仍然开的丰满茂盛。父亲的脖子上挂着两刀猪肉和两条活鱼,这是小户人家请接生婆上门的喜礼,他将手里的长篙撑的又快又匀,在一片白茫茫的夜色中,小排在烟霭缈缈的河波深处摇动着,父亲的心也跟着竹排的浮沉摇动着。 接生婆进了屋子,过了好久,哇的一声,孩子落地了,九斤多重的大胖丫头,满头大汗的接生婆把我抱出来给父亲看,他吃吃笑了很久。 生想想那晚,我做了一个好暖和的梦,梦里面栗子熟了,柿子也红了。 凌晨一点零四分,精疲力竭过后的我神志迷糊,梦醒过来,助产士把一个红扑扑的小婴托举到我眼前,轻轻的跟我贴了一个面,虽然看不清楚,但我知道那是我的想想。 生她最痛的时候我瞳孔放大,几度晕厥,肝功能损伤,全身冰冷发抖没掉一滴眼泪,却在看到她静静躺在我身边的时候潸然泪下,第一次抱她,吻她的感觉让我如获重生。 小小的她像长在老家河岸边的一尾柔嫩白羽,又如刚刚出壳的雏雀儿,头发湿湿的,身子软软的,握紧的小拳头上有四个浅浅的梨涡,眉头紧蹙着,小胸脯起起伏伏好似河里的水波,呼吸如老家的山蜜那般香甜…多美的小天使,扑簌着翅膀越过山河,一个猛子扎进了我的怀里。 少年时候父母不在身边,我常跑到山上去采蕨,松风过耳,地里的野花开了一茬又一茬,养鸭人遗落在滩上的鸭蛋总是被我捡到,林子里的果子每次拾满一口袋便滴溜溜地掉下来…… 后来,我跋山涉水出去念书,一个人乘火车去远方工作,背着行囊远走他乡,生命最多的日子里,我学会最好的本领,就是跟自己独处。 直到她出现,我才渐渐走出自己的世界,她教会了我怎样做一个母亲。 回首这两年,就像小的时候在地里偷萝卜,枇杷树上摘枇杷,过程很苦涩,但结果却是甜的。她比少年时候,那枚鸭蛋,那朵野花,那颗果子,那阵山风,那些走过的地方,更让我觉得暖和,觉得满足。 想想生在秋末冬初,这个时节,山里的果子们越过了树篱,叶子们簌簌远去,一心挣脱离开母体。对于人间草木来说,子女的成长是一只看不见的手,寒来暑往的对抗,却终究抵不过一阵微不足道的秋风。 万物皆有定期,父母的脚步,大概在孩子诞下的那一刻,就悉数递减了吧。 有一次收拾母亲的衣柜,在柜子顶上抽出来一只雕了花的木箱,用缎布盖着,沉睡了很多年的样子。我小心翼翼的打开箱子,竟然抖落出了好些母亲年轻时候穿的裙子,裙子的颜色都很沉稳,绿是老油画里的湖绿,蓝是暗格印花的灰蓝,红是几近裸色的藕粉,白是不扎眼的古拙棉麻,每一道手工压制出的线条肌理都捻进了时光里,一寸一寸催人老。 原来母亲也曾美过呀,什么时候呢?我不敢把面前这个声音洪亮,头发渐白,衣着简朴,皮肤皴黑的母亲联想到一处。可记忆深处某个清晨,公鸡一声声啼鸣,我从暖和的被窝里探出头来,看见一个年轻妇人穿着一件草绿色的风琴折裙坐在镜橱前盘头发,挺直的背犹如山里的青竹,柴火锅里的粥香从半掩的门缝中飘了进来……好一个温暖的秋梦。 有一次带着孩子回娘家,平日寡言的母亲跟我絮叨了好多我与弟弟孩提的趣事,她身上熟悉的青蒜菜油味儿让我安适,忽然屋里传来一声婴啼,我急得丢下仍沉浸在往事中的母亲,飞奔进屋,再抱着孩子回到母亲旁边的时候,只听得她笑叹了一声:我都忘了,你都嫁了… 几十年过去,母亲苦追我们的背影,追到步履蹒跚,追到头发都白了,而我们就像欢脱的小兽,走马观灯花红柳绿,跟着不露锋芒的时间跑啊跑,背后牵引我们的线一处一处断,一片郁郁中,母亲孤零零地再看不见我们。 山里人说,冬天胃里暖和了身子才会暖。人们总在冬天怀旧,寒夜也总能催人想家。天寒地冻时候,一碗白粥,一碟咸菜,一罐辣酱,一条腊肉,一瓮豆腐汤都会让人想到家乡的母亲。一想起故乡,就会想到母亲做的饭,胃如炭焙,身心俱暖。 板栗落了,**仍开着,秋桂凋零,冬柿却一枝枝红着。母亲老了,孩子们长大了,一年也就这么过去了。